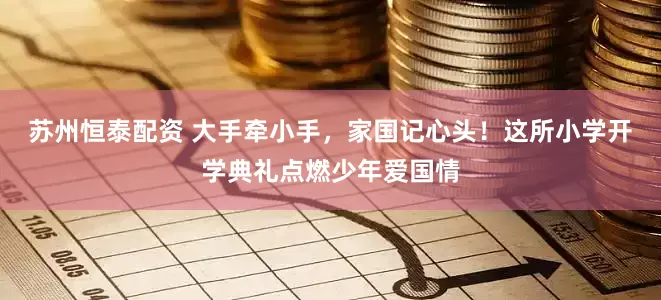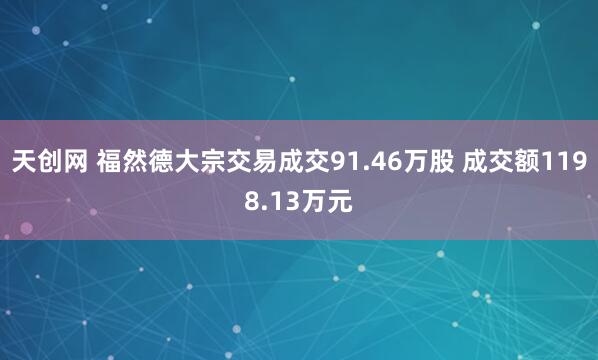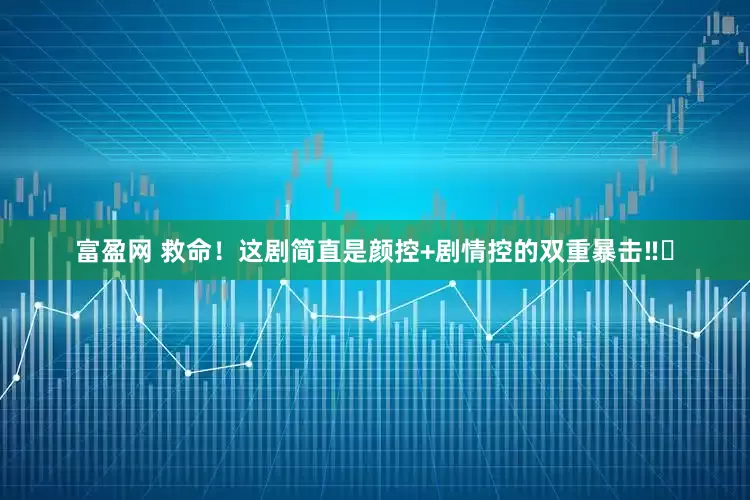大明首封襄王朱瞻墡(音shàn)寻钱网,为明仁宗朱高炽与发妻诚孝昭皇后张氏的幼子,是大明宗室之中有名的贤王,一生经历堪称传奇,不仅出任过监国,还三次传言他这一脉将继承皇位(两次为其本人,一次为其嫡长子),然而非但没有引起皇帝的猜疑,反而深受皇帝礼遇,得以善终,身后以“宪”作盖棺定论。史书给予的评价也极高:
“王于诸王中为最亲,故朝廷所以眷爱之者为最优。王小心清慎,笃于孝敬,尤为诚孝昭皇后所钟爱。然能守礼法,远嫌疑。故虽有异议,不为上下所疑。卒能安荣寿考,以终其天年。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)
襄阳襄王府

襄宪王能在云谲波诡的政局中全身而退,固然与他谨守礼法、小心清慎、笃于孝敬以保禄位的做法有关,也与其偶尔为之的黑历史脱不了干系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位大明最牛皇叔的阴暗面。
缘起
事情还要从土木堡之变说起。
正统十四年(1449年)八月十五日,“英明神武”的明英宗朱祁镇陛下,把大明精锐和自己当做过节大礼包一并送给了大明淮王殿下、瓦剌太师也先。
消息传回京师,从孙太后到朝野无不大惊失色,皇帝被俘,群龙无首,虽有皇嗣,可最年长的朱见深也才两岁,国难当头有赖长君,让他监国或称帝显然不合适。
其实明英宗亲征前,便有过安排,效仿父皇当年亲征汉王之策,令时年22岁,尚未之国的郕王朱祁钰居守。照理直接让他监国主持朝政便是。
可孙太后有自己的想法,郕王也是先帝之子,让他主持大局一但成功,很容易反客为主,携势自立为帝。而她与郕王母子关系很一般,朱祁钰生母吴贤妃尚在人间,若郕王称帝,定然会尊崇生母,冷落她这个嫡母,到时候让她自己,让好大儿及小孙孙们如何自处。
关键时刻她想到了宣庙的胞弟、自个的小叔子襄王朱瞻墡。虽然宣庙驾崩时一度传出宫中欲立他为帝的传言,可传言毕竟是传言,没有实证,且襄王远在湖广襄阳府,让襄王赴京监国,一来路途遥远,极有可能尚未到任,亡国危机便得以消除,无需再让他监国,二来再怎么样,身份毕竟隔了一重,对自家好大儿、对几个小孙孙的威胁性无疑更小。
两相其害取其轻,这一点孙太后还是懂的。
然而决定死保京师的官员们,更需要一位近在眼前的领袖,而非远在天边的虚君。于是乎朝臣们在朝堂之上给孙太后表演了一番什么叫君子六艺。眼见于此,孙太后不得不一步步退缩,先是于八月十八日命郕王监国,后于九月初六立朱祁钰为帝,遥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,换取册立长孙朱见深为皇太子。
明代宗剧照

等到明代宗朱祁钰病重,因其无嗣,朝堂之上就继承人选问题又闹得不可开交,一派主张立前皇太子、现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,一派建议迎立襄世子朱祁镛。
也正因此,当明英宗在景泰八年(1457年,也即天顺元年)正月十七日复辟后,对自家嫡亲五叔及其不信任,史载“帝颇疑瞻墡”,认为“迎立外藩”事件中有襄王本人的手笔。
好在其后明英宗在查询早年无意间找到了两份涉及襄王的奏疏:
其一为:“诸王中,瞻墡最长且贤,众望颇属。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,不果召。瞻墡上书,请立皇长子,令郕王监国,募勇智士迎车驾。书至,景帝立数日矣。”(《明史·诸王传》)
也即面对大嫂的召唤,朱瞻墡非但没有应召,反而上疏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:立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,命郕王朱祁钰监国,以稳定人心,同时选派人手营救被俘的留学生。只是此奏疏送抵京师时,明代宗早已登基称帝,令他颇为尴尬。
其二为:“英宗还京师,居南内,又上书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,率群臣朔望见,无忘恭顺。”(《明史·诸王传》)
明英宗回到京师后,明代宗虽碍于兄弟情谊没有弑兄,却将其囚禁于南内,一关就是七年之久。对此,朝野几乎万马齐喑,作为皇叔的朱瞻墡却站出来为大侄子向小侄子求情,让他善待兄长。结果如何,历史已经清晰的展示给大家伙。
也就是说两件事情,朱瞻墡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目的,可关键时刻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。明英宗发现这两份奏疏后大为震动,加之急需树立典型,为自己挽尊,于是乎对襄王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。
劝皇帝挖绝户坟
天顺元年(1457年)三月十三日,因册立皇太子及册封诸子,给诸王致信,其中当来少不了襄王的一份。可在此之外,明英宗又单独给五叔去信,盛赞“叔父之心,即周公之心,而此二章,亦即金縢之书之比也。”同时对朱瞻墡奏请赴京朝觐之事做出批示,表示“本不敢烦远来,第念先帝同气至亲惟叔父,宗室至贤亦惟叔父。于情于谊,不可不重欲得一见,以笃亲亲”。
明英宗剧照

此举算是开了自宣德朝以来的先河(此前为奔丧,性质稍有不同)。四月二十一日,襄王朱瞻墡抵京,皇帝陛下给予了隆重的接待,命文武百官赴诸王馆朝见。
虽然大侄子的态度发生了惊天大逆转,可谁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,为摘清自己,表达决无染指皇位之意,他在朝觐期间做了一系列努力。比如奏请营建景泰年间便已批复的南漳五朵山园寝。再比如,奏称宣德年间大兄宣宗皇帝特恩另赐乐人二十户,但宣德、正统、景泰三朝皆未实际赐予,废帝甚至违背大兄遗命直接不许,如今自己垂垂老矣,幸逢皇上开创太平盛世,正宜鼓缶怡乐之时,请求如数赐予。明英宗龙心大悦,命湖广布政司于所属府州县乐户内拨二十户与之。
以上只是为表明自己政治态度,属于守势。在此之外襄王殿下又主动出击,以讨好皇帝大侄子,那便是建议毁寿陵。
景泰七年(1456年)二月二十一日,明代宗的第二任皇后杭氏崩逝。杭氏,本是郕王侍妾,因于正统十年(1445年)二月二十日,生下朱祁钰的长子兼独子朱见济,而母以子贵,最终得以在景泰三年(1452年)五月初二进封皇后。
明代宗虽领导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而声威大震,可按照当初的约定,他的帝位只属于终生制,而非世袭制,驾崩之后需传位于大侄子朱见深。登基之初,被内忧外患所困扰,朝不保夕之下自然没有多余想法,但伴随着政局稳定,内心便发生了巨大改变,谋求万世一系成为执念。
景泰三年五月,通过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寻钱网,改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的方式,总算达成自己的目的。然而好景不长,次年十一月十九日,朱见济这位新任皇太子不幸薨逝,年仅九岁,赐谥曰怀献,葬于金山。
皇帝膝下空悬,储君之位出缺,让本就对废立皇太子事件大为不满的群臣找到了宣泄口,纷纷上疏要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。
对明代宗而言,自己年岁尚不足而立,正是生育的黄金时间段,有大把的机会生儿子,又岂肯把力争来的储位让出去。何况即便把皇位还给大侄子,因此前的冲突,谁知道百年之后对方会如何安排自己。
明十三陵

也正因此,让他低头是万万不能的。但文官们好不容易找到机会,岂会善罢甘休。是以其后数年之中,尽管有御使因此下狱并被活活打死,却并没有不文官集团唬到,前仆后继的大有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。
杭皇后的去世,无疑给了明代宗一个反击的绝佳机会:借着给皇后造陵寝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。这是有先例可循的,孝慈马皇后与仁孝徐皇后皆先皇帝而去,太祖高皇帝和太宗文皇帝为此兴建给自己的寿陵(指帝后生前预筑的陵墓),文皇帝还借此奠定了迁都的基础。
有先例在,自己完全可以抄作业。
为此,明代宗一面按昭穆之制在天寿山陵区献陵之右,迅速选定陵寝位置,命太监曹吉祥、保定侯梁珤和工部右侍郎赵荣督造,并动用四万名官军日夜赶工。一面命文武百官到思善门外行哭临礼,并让礼部拟定杭皇后的谥号:“肃孝”。
当年五月底,寿陵玄宫落成,明代宗名之曰寿陵,并按照传统设立寿陵祠祭署,拨顺天府昌平县民五十户看守陵寝,改武成中卫为寿陵卫。也就是说寿陵自一开始便具有了皇陵的规格。六月十七日,肃孝皇后梓宫发引,二十二日入葬寿陵。二十五日神主回京,随即升祔于太庙。
这一系列操作,是否有种熟悉的感觉?
对,没错,五十年前明太宗陛下这么操作过,百余年后的老道士也是这么操作的。要知道当年马皇后去世后,神主安放于奉先殿,而非太庙。所以这一操作,差不多成为大明小宗入主大宗的标准流程了。
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,明英宗复辟,开启朝堂大清洗。二月初一,站稳脚跟的明英宗以孙太后的名义,下诏废朱祁钰为郕王,将其软禁于西内。当月十九日,郕王朱祁钰去世,年仅三十岁。
朱祁钰已不是皇帝,自然不能入葬天寿山陵区,故以亲王礼改葬于西山,与怀献世子(即朱见济)及许悼王坟园同处一地,并赐谥曰戾。谥法“不悔前过曰戾”、“不思顺受曰戾”、“知过不改曰戾”,说实话明代宗于江山社稷有大功,但“好哥哥”只记得他虐待自己,不论其他,直接恶谥开道。
寿陵的仪制也被废除,寿陵卫这个新设不久的陵卫,重新恢复武成中卫之名,从中调拨旗军三百户看守郕戾王坟园。
做完这一切,能彰显朱祁钰皇帝身份的,只剩下天寿山寿陵。寿陵自然成为明英宗的眼中刺,成为下一个目标。何况杭氏的皇后封号也已被废黜,再让他沉睡于帝陵之中,实属僭越。
当然他身为皇帝,直接开口掘坟毁陵,实在有失体统,这时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干脏活,这也是上位者身边往往会围绕着几个小人的根本原因之一,毕竟随时有人充当自己出声筒的感觉相当美好。
长陵明楼

明英宗身边自然有出声筒,可身份不太合适,容易遭来非议。恰好襄王来京,一方需要有分量的出声筒,襄王作为先帝的胞弟,身份尊贵,由他开口可以压制各种杂音;一方虽获得皇帝谅解,可唯恐大侄子过后给自己小鞋穿,急需机会表忠心。于是乎双方一拍即合。
按照惯例,亲王赴京朝觐,也需赴山陵祭祀诸帝陵寝。襄王殿下此次朝觐大侄子,也依例赴天寿山,祭祀长陵、献陵、景陵。
自天寿山返回后,朱瞻墡捏着鼻子给大侄子上疏,奏称自己祭祀山陵过程中,看到郕王安葬妾室杭氏之地明楼高耸,规制与长陵、献陵相同,简直是视礼制为无物。更过分的是景陵的明楼到现在都未建成,为人子者如此不忠不孝,臣实在是痛彻心扉、悲愤难忍。
随即话音一转,痛斥郕王“乘危篡位”,杭氏“越礼犯分”,表示陛下您忍得了,臣可忍不了,寿陵这个僭越礼制的违章建筑,必须立刻、马上予以拆除。
明英宗闻言大喜,假惺惺的表演一番后,于当年五月十一日,命工部尚书赵荣这位当年寿陵的督造者,调集长陵卫、献陵卫和景陵卫共五千官兵将整个陵区彻底捣毁,留下的遗迹史称景泰洼。至于杭皇后的梓宫,去向成谜,很可能被一并毁。
“其郕王祁钰承皇上寄托之权,而乃乘危篡位。改易储君,背恩乱伦,荒淫无度,几危社稷,岂特昌邑之比乎?幸遇皇上豁达大度,宽仁厚德。友爱之笃,待之如初。又存其所葬杭氏僣拟之迹而不废。虽圣德之可容,奈何礼律之难恕。伏望夷其坟垣,毁其楼寝。则礼法昭明,天下幸甚。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)
劝皇帝拆寡妇门
劝皇帝挖绝户坟,让襄王殿下收获了巨大的利益,比如大侄子准许襄藩组建自己的护卫:襄阳护卫,成为自宣德以后唯一一个获得护卫的藩国。又比如,准许襄王父子每年可以不经奏请,自行出城游玩数次,在藩禁森严的时代又是一项莫大的恩赐。
天顺年间,在藩王朝觐制度名存实亡的状况下,朱瞻墡获准两度赴京朝觐,平日里叔侄俩书信往来平凡,各种赏赐不断,都离不开襄王殿下关键时刻识时务的表现。
有了这一前例,朱瞻墡自然会再接再厉。
天顺八年(1454年)正月二十七日,朱瞻墡上疏朝廷,奏称皇次子德王朱见潾出府别居——即离开皇宫,前往诸王馆开府——可郕王妃汪氏依然居住于此,多有不便,建议将她们一家子前往别处居住。
王府井大街:明朝十王府故址所在

然而这次,襄王殿下的马屁却拍在了马蹄上。奏疏发出没多久,他便接到来自京师的“讣音”:当朝皇帝朱祁镇已于本月十七日驾崩,遗诏皇太子朱见深继位。
明宪宗这位新皇帝,对叔祖的这封奏疏进行了回应,可内中充斥着嘲讽的意味:
“上曰:‘叔祖所言良是。但郕王妃寡居,孤女未嫁。始自西内迁居外第,盖先帝盛德事也。今若他徙,无所于归,其勿复徙。’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)
明宪宗因幼年的经历,总体而言对宗室相当宽容,为何会如此不给叔祖留面子呢?还要从皇室内部纷争说起。
所谓的诸王馆,又名十王府,是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,与紫禁城同时建造的一组配套建筑群,位于皇城东墙外,地处东安门外东南方向,东西宽约200米,南北延伸近500米。其故址在今北京王府井大街以东、金鱼胡同以南,覆盖今校尉胡同至大甜水井区域。
其主体建筑群包括:围墙环绕的封闭式院落群,官署、营房等附属设施,配套水井。主要用于安置出阁后未就藩的亲王和来京朝觐的宗王。该区域因十王府而得名“十王府街”,满清入关后改称“王府大街”,清末因街南端的甜水井(十王府配套水井)又更名为“王府井大街”。
郕王妃汪氏,为明代宗朱祁钰的原配,第一任皇后。景泰三年(1452年),明代宗欲废侄子朱见深这个太子,改立杭氏之子朱见济为皇太子,汪皇后强烈反对,因此触怒皇帝,直接废后,改立杭氏为皇后,汪氏移居别宫。
正是这一段经历,彻底改变了汪氏的人生轨迹。
明英宗复辟后,朱祁钰被废为郕王,被废的汪氏再次被册立为郕王妃。囚禁于西内的郕王很快病逝,此时殉葬制度依然在运转,郕王的妾室统统被殉葬。郕王妃汪氏没有子嗣,是否殉葬处于两可之间。
关键时刻,深得明英宗信任的礼部尚书、内阁大臣李贤站出来为汪氏说话,表示其在景泰朝已废且幽禁深宫,况所生两女年幼,不当予以殉葬。明英宗清楚她乃是为保全自己儿子被废,故并没有为难这位弟媳,直接将她们母女迁至位于十王府的郕王府安居。
明英宗如此,当事人明宪宗对这位婶婶自然更为感激,对她和两个堂妹颇为照顾。自迁居郕王府后,汪氏历经四帝,直到正德元年(1506年)十二月才去世,享年80岁。去世后明武宗尊谥“贞惠安和景皇后”,与明代宗朱祁钰合葬景泰陵。南明弘光帝即位,改上谥号孝渊肃懿贞惠安和辅天恭圣景皇后。
可以说明宪宗及其后代,对汪氏这位郕王妃都礼遇有加。关键襄王殿下这一奏疏的目的,也并不那么纯粹。
明代宗原配汪皇后剧照

无论你对明朝诸帝持何种态度,可有一点绝对无法否认,绝大多数皇帝都很专情,明太祖如此、明太宗如此、明宣宗亦如此,最出名的当属明孝宗。
明英宗虽多有不堪,可他与钱皇后这对少年夫妻感情,却无可挑剔。正统年间即便是庶出子女接连降生,而钱皇后毫无动静,也没有学父皇提早立太子,更没有动过废后的念头。土木堡之变后,皇帝留学瓦剌,钱皇后心急如焚,多方设法营救,最终残了一条腿,瞎了一只眼,连生育能力都因此丧失。明英宗回来后,二人又在南内患难与共。
但有些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明英宗复辟后,立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,其生母皇贵妃周氏眼见皇后丧失生育能力,想到婆婆孙太后母凭子贵正位中宫的往事,不禁心驰神往,想方设法的诋毁、排挤钱皇后。
钱皇后能将皇帝的心拴在自己身上,自然也不是什么白莲花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周贵妃,她也进行了反击,出招不多,只有两式。
天顺六年(1462年)九月,孙太后去世。随即齐纳皇后出面出面力劝明英宗恢复宣庙元后“静慈仙师”胡善祥的皇后名分。对其目的心知肚明的明英宗当即应承,认下胡善祥的嫡母身份,尊谥“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”。“章”是明宣宗的谥号,在明代只有原配可以祔帝谥并祔祀太庙,继后及追封皇后没有这两项权利。
一个皇帝,为了身体残缺的发妻身后事,竟违背先帝生前的诏令,硬给自己找个嫡母,将废后重新推上位,并让自己老娘因此痛失祔祀太庙常伴先帝的荣耀,也算是用情至深了。若是明宣宗与孙皇后泉下有知,估计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个有了老婆忘了娘的逆子。
给予胡善祥元后身份属于守势,钱皇后的手腕自然不止于此,她还亲自抚养皇次子德王朱见潾。按照传统,皇后无子,那么其抚养的皇子可视为嫡子,理论上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。要不是这是比较注重父子亲情的朱明皇家,要不是朱见深一早就被立为皇太子,并被满朝文武所公认,仅凭这一手,兄弟俩就要爆发一场夺嫡之争。
即便如此,依然让人浮想联翩。
天顺七年(1463年)八月十八日,时年16岁的朱见潾正式搬离皇宫,入住位于十王府的临时驻地:德王府。襄王朱瞻墡得知德王出府,竟派人送来厚礼。要说他没提前嗅到什么,很难让人信服。
“癸卯……复书襄王瞻墡曰:‘近以次子德王见潾年长,令其出府,此亦常典。乃荷叔父重亲爱之念,赐之礼物,兼示诲言,欲其隆孝敬,励学问,节用爱人,亲贤乐士,皆格言也。非叔父贤明,曷克臻此!深感!深感!已令德王佩服嘉训,用图成德。专此奉复。’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)
明宪宗剧照

事实上德王朱见潾与襄王这位叔祖有些类似,明英宗病危之时宫中一度传出更换继承人的传言,更立的对象会是谁不言可知,只是被内阁首辅李贤等重臣压下,才没能如愿。明英宗遗诏中特地废除殉葬,强调要皇太子善待嫡母,善待德王,估计也与此有关。
是故朱瞻墡这位叔祖一而再拿德王向先帝示好,甚至为此拿对朱见深有恩的郕王妃汪氏开刀,坐上皇位的明宪宗内心必定如吃了苍蝇般恶心,只是去信阴阳下襄王已属宽宏大量。
阿越说
“守礼法,远嫌疑”,这六个字高度概括了襄宪王朱瞻墡一生的行为准则,也正因此他这一辈子虽三次传言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,却能历经七朝依旧安然无恙,乃至获得朝廷非同一般的礼遇,平安终老,成为明仁宗诸子中最晚去世,也是最长寿的存在。
这一切除明哲保身之外,也与他适时站队,积极表忠心也有着重要关系。不过有时候,忠心与良心无可兼得,表了忠心,就要违背良心。忠心与良心之间,朱瞻墡做出了选择。
上疏力劝明英宗挖绝户坟,虽然有违良心,但多少也算是紧跟时代需要。可换得的丰厚奖赏,令朱瞻墡有些飘了,以至于连储位之争这等对他这等藩王而言属于绝对禁忌的活动,都打算插一手。结果竹篮打水不说,还恶了新皇帝。好在明宪宗这位侄孙还算开明,虽有针对之举,却不算太过分。
所以人啊,还得学会守住本心,不忘初心。
同创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